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
税收体系一般指政府通过立法所确立的各类税种之间所形成的关系,这样的关系又决定着各类税种在国家税收总额中的比例构成,即税收结构。随着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形势的演变,有唐一代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多有发展变化,尤以中唐时期为剧烈,并以德宗建中元年(780年)租庸调制的最终废弃和两税法的全面实行为分界,形成前后两个时期各具特色的体系与结构特点,直接影响了宋代以后的国家税收形态,在中国封建税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。以学界关于唐代税收制度的丰硕成果为基础,结合个人学习探索的一孔之见,概要阐述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的发展变化情形,以图从一个层面观察唐代社会乃至中古封建社会的前后变迁。
唐前期的税收体系和结构
唐前期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农业税是最主要的税种,长期支撑了国家财政。同时,按照土地和财产征收的地税与户税,以及附加于租庸调、地税、户税之上的多种附加税,也是重要税种。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瓦解,租庸调征收在国家税收总量中的比例趋于下降,地税、户税和附加税的比例逐步提高,税收结构发生了由税人为主向税地、税资产为主的明显变化,为后来两税法的实行奠定了基础。以下通过对唐前期主要税种实际变化情形的简要考察,来予以具体阐述。
1.租庸调农业税及其折纳形式
唐王朝建立后,继续推行北朝隋代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,授予广大民户以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,(注:均田制所规定的授田数额只是原则上的,实际授田普遍不足(甚或不授),也只是授予国有无主荒地,并不触动所有权明确的私有土地。)使其从事耕织生产,能够有能力负担国家赋役。同时推行严格的计帐制度和户籍制度,“每一岁一造计帐,三年一造户籍。县以籍成于州,州成于省,户部总而领焉”,[1](卷3《尚书户部》,P65)为均田民户建立起详备的档案资料。通过这些制度,既可实现著民于田,稳定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,又可适量调节贫富分化,保障封建统治秩序。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税制度。它规定:“每丁岁入租粟二石。调则随乡土所产,绫绢?各二丈,布加五分之一。输绫绢?者,兼调绵三两;输布者,麻三斤。凡丁,岁役二旬。若不役,则收其庸,每日三尺。有事而加役者,旬有五日免其调,三旬则租调俱免。”[2](卷48 《食货志上》,P2088-2089)又规定,“水旱霜蝗耗十四者,免其租;桑麻尽者,免其调;田耗十之六者,免租调;耗七者,课役俱免”。[3](卷 51《食货志一》,P1343)不过,租庸调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法律税制,在实行中又有其独立性,并不完全依托和建基于均田制,并不取决于每户和每丁实际授田是否足额,在没有复除、蠲免情况下,只要是在籍均田课户,户内有成年男丁,就要按照每丁每年相同的数额负担租庸调,被称为丁租、丁调和丁庸,实际上是按丁征收而不计田产,即计丁课税。执行统一的长期稳定的税收标准,仍是人头税。这表明唐王朝依旧采取了通过分配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以固着民户,并对民户实施超经济剥削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,承继了北魏、北齐和隋代以来的田制和税制。需要指出的是,租庸调制以丁为单位征收而不计占有土地与财产的多少,造成了税负的极端不合理。对此连唐人也不讳言,杜佑即说租庸调制“百姓供公上,计丁定庸调及租,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,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”。[4](卷7 《食货七。丁中》,P175)
在实际执行过程中,根据各地物产情况和政府具体需要,租庸调征收采取灵活变通、形式多样的折纳制,遵循定量折纳和等价折纳的原则。江南地区的丁租可折纳稻米,也可折纳布匹;河南、河北不通水运之处,丁租可折纳绢或米、豆;关中地区因为桑蚕很少,丁调可折纳米、粟;一些地方的丁调还可折纳金银、铜铁、宝货、绫罗等;唐前期允许盐业私营,私营生产者可以食盐或轻货折纳丁租。《新唐书》卷54《食货志四》载,“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,青、楚、海、沧、棣、杭、苏等州,以盐价市轻货,亦输司农”,就是海盐私营生产者将每年应交纳的丁租折成食盐或轻货而完税。井盐私营生产者多以实物纳税,武周时陵州盐井就实行税率为三分之一的分成税,即“置灶煮盐,一分入官,二分入百姓家”。[5](卷399《盐井》条引《陵州图经》)估计其他地区的井盐私营、池盐私营也行实物税,所税多少也应是折纳丁租等;在官营优先的前提下,唐前期也允许矿业私营,即所谓“凡州界内,有出铜铁处,官未采者,听百姓私采”。[1](卷30,州士曹司士参军职掌条)为了保障国家垄断铸币业,规定私营矿业所得铜、锡等铸币材料,要由政府一手买断,不得私自买卖和拥有。除此之外,唐政府对私营矿业还征收矿税-设冶监官营处的私营矿业,向当地冶监交纳矿税;不设冶监处的私营矿业,则向当地地方政府交纳矿税,也可以矿产向当地地方政府折充课役。[6]盐税与矿税的本质相同,都是租庸调的折纳形式,也都包含在农业税中。玄宗开元九年(721年)之前,盐税、矿税的征收已走上法制化的成熟轨道,政府制定了专门的“令”、“式”条文,规定“诸州所造盐铁,每年合有官课”。[7](卷88《盐铁》, P1902)盐税的法制化征收延续到肃宗乾元元年(758年)推行第五琦榷盐法,才由禁榷专卖制度代替了税收制度,矿税征收则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以后,只是管理比较混乱。
因地制宜的折纳形式多种多样,反映了租庸调制的变通性和灵活性,但大体不改变纳税总量和折纳总值,每丁负担的数额基本固定。租庸调及其折纳形式是唐前期最主要的税收,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,长期维系了唐王朝的财政命脉。但自高宗、武周以后,土地兼并愈演愈烈,土地私有化趋势难以遏止,国家掌握的授田土地越来越少,均田制到玄宗朝已全面废坏,广大均田民户的土地被吞并,纷纷逃亡或者成为贵族、官僚、地主的隐户,在籍丁口大幅减少,租庸调征收日益困难,税额锐减,财政地位急剧下降。安史之乱后,租庸调制徒存虚名,毫无实际意义。德宗建中元年(780年),租庸调制被唐政府最终废弃,代之以两税法,符合了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和社会财富极端分化的经济现实,标志着我国赋税史上计丁征税从此基本结束,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。[8]
2.地税和户税
地税和户税是唐前期与租庸调并行的另外两种国家税收,均属资产税,两税法实施后并入两税而不复独立存在。在实行过程中,地税和户税的税制不断完善,税额不断增加,玄宗后逐渐成为替代租庸调的主要财政收入,其税法税则还直接为两税法所继承,实现了税收制度的延续。
地税以建立义仓为名创行于唐太宗贞观二年(628年),王公以下人户的所有垦田皆须交纳,规定“亩税二升,粟、麦、粳、稻,随土地所宜。宽乡敛以所种,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。田耗十四者免其半,耗十七者皆免之。商贾无田者,以其户为九等,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。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。岁不登,则以赈民;或贷为种子,则至秋而偿”,[3](卷51《食货志一》,P1344)确立了税法、税则以及蠲免事宜。高宗永徽二年(651年),对地税制度做了改革-“义仓据地收税,实是劳烦。宜令率户出粟,上上户五石,余各有差”,[2](卷49《食货志下》,P2123)把地税由按亩征收改为按户等征收。到武周初年恢复为按亩征收。[9](P209)玄宗朝继续征收地税,税制更加完善。[1](卷3《尚书户部》仓部郎中员外郎条)肃宗、代宗时期,地税税率不断提高,税额大幅增加,并开始分夏、秋两次征纳。[10](P194-195)与租庸调制不计授田是否足额,按丁征收统一的丁租不同,地税按照王公以下每户实际耕田面积征税,显然有其明显的合理性,也有调节贫富差距的积极意义。
地税以义仓为名,是赈灾专项粮储,武周以前,“数十年间,义仓不许杂用”。[2](卷49《食货志下》,P2123)中宗神龙前后,国家财政拮据,义仓粮食不再用以救荒,而被挪用填充亏空。开始发挥财政作用,地税制度性质发生了变化。玄宗朝,将地税征收与租庸调征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,曾设立了勾当租庸地税使专门负责,有时也派监察御史分赴各地督促征收,地税被更广泛地用于财政支出,并大量变造为米运往京师长安,成为一项重要税收。《通典》卷6《食货典。赋税下》载天宝年间天下计帐,其中“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”。当时全国课丁820余万口,扣除各种折纳后,实际“租粟则七百二十余万石”,地税所得大大超过了丁租实际所得。《通典》卷12《食货典。轻重》载天宝八年,“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”,其中“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”,占了65%以上。地税成了国家的主要税粮,其财政地位日益重要。
户税亦创自唐初。高祖“(武德)六年三月令:‘天下户量其资产,定为三等。’至九年三月,诏:‘天下户立三等,未尽升降,宜为九等。”[4](卷6《食货六。赋税下》,P106)在编制户籍时一并确定。户税就可能开征于此期,按照王公以下每户资产的多募交纳数量不同的资产税(有时也折征实物),遵循以支定收的原则,并有大税、小税、别税之别-“凡天下诸州税钱,各有准常。三年一大税,其率一百五十万贯;每年一小税,其率四十万贯,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。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,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”,[1](卷3《尚书户部》户部郎中员外郎条)各有其财政用途。与租庸调制相比,户税不分课户、非课户,也不分主户、客户,王公以下的人户均要交纳,纳税面十分宽泛,其中对工商业户的完税管理更为严格,严禁工商业者勾结政府官吏以降低户等,少交户税。[7](卷85《定户等第》,P1846)
玄宗开元年间户税已每年分两次征收,定额不断扩大。天宝年间, “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,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”,[4](卷6《食货六》,P110)广泛地用于宫俸等各类财政支出,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,财政地位日渐重要。[11](P499-500)安史之乱后,户税愈加受到重视。大历四年(769年)正月,代宗敕令:“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,分为九等:上上户四千文,上中户三千五百文,上下户三千文;中上户二千五百文,中中户二千文,中下户一千五百文;下上户一千文,下中户七百文,下下户五百文。其见官,一品准上上户,九品准下下户,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。若一户数处任官,亦每处依品纳官。其内外官,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。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,不在税限。其百姓有邸店、行铺及炉冶,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,依此税数勘责征纳。其寄庄户,准旧例从八等户税,寄住户从九等户税,比类百姓,事恐不均,宜各递加一等税。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,无问有官无官,各所在为两等收税。稍殷有者准八等户,余准九等户。如数处有庄田,亦每处税。诸道将士庄田,既缘防御勤劳,不可同百姓例,并一切从九等输税。”[2](卷48《食货志上》,P2091-2092)对户税制度做了改订和调整,规定了官僚、百姓、工商业户、寄庄户、寄住户、浮客及诸道将士的级差税额,完善了税法税则,大幅提高了税率,进一步扩大了纳税面,户税总额有了显著增长,其财政地位更加突出。户税不论主客浮寄、以支定收的原则和每年两次征收的方法,均直接为后来的两税法所继承。
3.附加税
指附加于租庸调、地税、户税上的税收,有脚钱、营窖、税草、加耗、裹束等,在唐前期均形成为固定税制,但不是主要税种。脚钱(亦称租庸脚直、脚直、脚价、租脚、车脚或运脚等)是各州租庸调和地税送纳配所以及运至两京所需加纳的运输费,通常交纳铜钱,可按户配脚,也可按丁支脚。[4](卷6《食货六。赋税下》)由于各地路程的远近险易不同,中央度支虽然规定了脚钱征收的基本数额,但具体征收各地有所不同,[1](卷3《尚书户部》度支郎中员外郎条)营窖税是为了营建仓廪和保存粮食而附加于丁租、地税之上的附加税,规定征藁、橛、蘧chǘ@①、苫等实物,[1](卷19《司农寺》太仓署令职掌条)实际征收中,由于实物不易运输,多折纳现钱。税草是地税的附加税,始征于太宗贞观年间,同地税一样按照青苗簿每年征收,百姓均田、寺田、观田均需交纳。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五百里之内州县,不但有常税草供诸闲厩马料,而且有别税草供皇帝临幸之用。两京五百里之外的州县税草,纳于当地,供州县军事、邮驿、运输等的草料支用,遵循按支定收的原则。加耗是丁租、地税的附加税,大体遵循“贮经三年,斛听耗一升,五年以上二升”[1](卷19《司农寺》,P375)的加耗率,即有1%和2%的不同比率。裹束是附加于庸调的包装费-“诸庸调物……所须裹束调度,折庸调充,随物输纳。”[4](卷6《食货六。赋税下》)征收这些附加税,唐王朝就征收了租庸调、地税、户税的运输、保管、损耗费用,使得租庸调、地税、户税成为了国家财政的净收入。
下一篇:金融税制需要改革



 新用户扫码下载
新用户扫码下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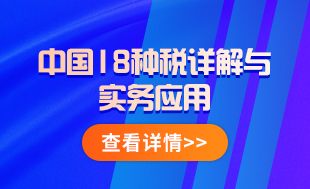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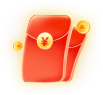

 新用户扫码下载
新用户扫码下载

